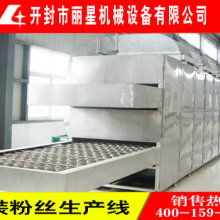穿过时光的帷幕,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一股混合着麦麸粉尘、机油与粮食原香的独特气味便扑面而来。这里,便是生产队时期乡村的“心脏”之一——粮食加工厂。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,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容器,承载着从田间到碗边的最后一道工序,也见证着一个村庄最朴素的协作与期盼。
轰鸣声中的生活交响
那时的加工厂,通常是几间高大的砖瓦房,屋顶耸立着粗壮的烟囱。最醒目的便是那台或数台庞大的机器——钢磨、碾米机、粉碎机,它们由一台突突作响的柴油机或电力马达带动。一旦开机,整个厂房便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与有节奏的震动中。这声音对于村民而言,并非噪音,而是收获季节里最动听的背景乐,是生活踏实向前的笃定鼓点。
大人们扛着一袋袋晒干扬净的小麦、稻谷、玉米排队等候。孩子们则好奇地在周围穿梭,看着金黄的谷粒从机器顶端的漏斗倾泻而下,经过内部铁质滚筒的碾压、摩擦、筛分,魔术般地从不同出口分流出来:这边流出的是雪白或微黄的面粉、米粉,那边落下的是较为粗糙的麸皮、米糠。空气中弥漫着细微的粉尘,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束里飞舞,给忙碌的人们身上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。
工序里的智慧与温情
加工绝非简单的“一进了之”。它有一套默守的流程和讲究。小麦通常要先“润麦”,适量洒水静置,让麦粒皮层柔韧,便于剥离,又能让胚乳适度软化,磨出的面粉更白、更筋道。碾米则要控制好碾磨的压力和时间,既要脱去谷壳(糙米),又要尽可能保留大米表层的营养成分,不过度打磨成精白米。有经验的老师傅,听听机器运转的声音,看看出粉出米的成色,就能判断粮食的干湿度和机器的状态。
加工费往往不以现金结算,而是留下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“加工损耗”或报酬。这本身也是一种朴素的物物交换和集体所有制的体现。等待间隙,乡亲们会互相查看成色,交流今年的收成,谈论家长里短。谁家磨的面粉特别白,会引来羡慕;谁家孩子抓一把刚出来的炒面(炒熟的谷物磨成的粉)塞进嘴里,会被大人笑骂一句“馋猫”。这里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情味。
麸皮与米糠:资源的极致利用
加工后的副产品——麸皮和米糠,在今天看来或许是饲料,在那个年代却是重要的补充资源。麸皮可以掺入主食,做成麸皮馒头、饼子,弥补细粮的不足。米糠则可以用来榨取珍贵的糠油,或者喂养家禽家畜。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分被浪费,“颗粒归仓”的精神一直延伸到加工的最后一环。孩子们有时会偷偷抓一把带着余温的米糠,嗅闻那特有的谷壳芳香。
记忆的坐标与消逝的风景
对于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而言,粮食加工厂是儿时记忆里一个鲜明的坐标。它关联着新麦入仓后的第一顿手擀面香气,关联着过年磨糯米粉做汤圆的期待,也关联着机器轰鸣声中那份集体劳作的踏实感。它象征着一个自给自足、节奏缓慢的农耕生活闭环。
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,生产队集体性质的加工厂逐渐完成了历史使命。高效率的现代化面粉厂、大米加工企业取而代之,家用小型电动磨粉机、料理机也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昔日轰鸣的厂房大多寂静、破败,或已拆除,只留在人们的记忆和泛黄的照片里。
每当提及,那种混合着机器声、粮食香和人情味的复杂感受便会苏醒。它不仅仅是对一种旧式生产场所的怀念,更是对一段共同经历、一种邻里互助生活方式、以及食物从源头到成品那份可触可感的珍贵历程的深深眷恋。在那个加工厂里,每一捧面粉、每一粒大米,都看得见来路,都凝结着汗水与阳光,也都散发着最本真、最踏实的生命温度。